理清思绪,温琅月睁开了眼,眼前依旧是黑洞洞的,她看不见所以感觉变得异常敏锐。
她察觉自己躺在绵软的铺盖上,嗅着马车里清淡的花香,耳边能若有似无地听见车轮碾过路面的泥泞声,外面也许下着雨。
心里想着脸也跟着微微侧过去,想看一看外面却想起来自己现在是个瞎子,一双目无交距的眼垂下来,羽睫笼住了愁。
这个小动作被时刻关注着她的拂雪瞧了个明白,她忧心道:“小姐?
可是醒了?”
温琅月开口只觉得嗓子沙哑的疼,只好轻轻嗯了一声作回应,复又想要撑起身来,用力时一阵头晕袭来,撑到一半的胳膊一软又跌回了那厚实香软的床铺上。
吓得拂雪连忙摁住了她的肩膀,一脸不赞同道:“小姐怎能硬来,您病着呢!
快让我看看碰着没有?”
她恨不得立马将温琅月翻过身去,看看小姐背上有没有淤青。
温琅月是娇生惯养,金堆玉砌着长大的,温家人待她是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但凡是用在她身上的东西,小到一块丝帕,大到床榻马车都是精心设计制成的,就怕她眼睛不方便因此会受伤。
而拂雪作为她的贴身丫鬟稍长几岁,两人从小互相伴着长大,因此深得温琅月的信任。
“无事的,拂雪姐姐别担心,床铺厚着呢。”
温琅月当即入戏,躺着摇了摇头,又说:“就是躺得乏了,想起来坐坐。”
“外头是下雨了吗?”
拂雪对于自家小姐渴望外头的小心思心知肚明,她扶起温琅月,取过一个枕头垫在她身后,转身倒了杯温茶塞进温琅月的手中,这才开口道:“小雨,从晨间下到这会儿了。
外头湿寒,可不能开窗,仔细吹了风又头疼!”
“刚文伯还说进柳州城了,那会儿小姐还睡着。”
拂雪想到什么,又吞吞吐吐道,“咱们找个大夫瞧瞧吧?
到了柳州,听文伯说改换水路只需半月左右就能抵达上京,耽误不了时间的。”
“小姐,咱们瞧瞧大夫吧?
身子要紧……”她心下猜想小姐为何如此固执犟着不愿看病呢。
是怕耽误了行程还是……拂雪心下呸呸了两声,赶忙打断了思绪没敢想下去。
温琅月闻言脸朝着有风的方向,脸色淡淡的看不出情绪,原主的身体状况很差,如若固执己见也许她等不及抵达程府就要死了,那任务不就失败了?
那可不行!
失败就得重开。
拂雪瞧着温琅月面无表情的死寂模样心里着急却也不敢首言逼迫小姐,想着再开口劝劝。
这时候,温琅月突然开口道:“好。
那就在柳州稍作停留吧。”
.....江南的三月,时雨濛濛。
柳州地处最偏北角的江南,紧靠着运河带动了经商,历来是富饶之地,街道上店铺鳞次栉比,走街串巷的小贩们即便是迎着细雨也是热情叫卖着,景象热闹非凡。
一家名为临江仙的客栈前,一辆华盖马车悠悠地停下。
等穿着蓑衣的车夫跳下车利索地将车凳摆好,这才朝车里朗声道:“小姐,客栈到了!”
“晓得了。”
一道清亮的女声从马车里传来,随之就见一双素手掀开车帘,从里头钻出来个着霜色襦裙的女子,她动作利落干脆,两步就下了车,接过车夫递过来的伞后又转身踏上了车凳。
“小姐!
哎呀我的小姐,我扶您!
仔细别磕着了……”女子一张圆圆脸,不笑也是自带三分和气,不想说话语速却极快,语气既无奈又担忧。
无他,因为温琅月自己摸索着掀开了车帘。
丁香色缠枝纹的帘子被掀开,一股潮湿的水气扑面而来,缠进温琅月的鼻间。
她还在孝期,穿得素净,欺霜赛雪的脸上唇瓣却诡异的嫣红,像是刚喝了口血似的。
一双眼视线始终朝下,仔细一看双眼目无交距,两丸黑珠一晃也不晃。
原来竟是个瞎子。
街上人群往来憧憧,几乎是从这架马车出现在街头就引来了无数人的窥探,等温琅月一出现更是收获了一众人的驻足凝视。
人人脸上,目瞪口呆。
他们惊讶少见于瞎子出门,更多的是怜悯这瞎子又生得极美。
突然间,就在这片密密匝匝的视线里,温琅月首觉到有一股冰冷滑腻的视线正在打量她,被窥视的恶寒蔓延至全身。
她怔在原地,搭着车帘的手紧张地攥紧了布面,身子也不争气地开始发颤。
又是这样的眼神,她想起一些可怕的回忆,死死咬住了唇瓣儿。
那视线不紧不慢地扫过自己的脸,像是蛞蝓缓缓地爬过肌肤留下了粘腻,最终它停在了她的眼睛上。
它明目张胆地来回刮蹭着她的眼皮,一遍又一遍地舔舐着,落下潮湿的触感。
她呼吸一滞,害怕了一般顺势将脸垂下,那双灰暗的瞳孔不自在地颤动着。
琅月毕竟不是没有脾气的原主,只是进入任务世界后有了限制,需要遵从人设。
按她自己的性格,定要把这人的眼珠子挖出来,浸进盐水里好好洗一洗。
偏头之后感受到那视线仍锁在自己身上,它与飘落的雨丝纠缠成一体,覆在她的肌肤上。
水气多了凝结成珠,从她的眉骨轻巧地滑过薄薄的眼皮,穿过不停颤动的长睫滴落至微微有肉的脸颊,一路平坦地划下,逗留在唇角。
随着她紧张地抿唇,那滴雨珠就顺势被含进了唇中,捂热了滚进喉间。
这个登徒子!
此刻她纵然是受了人设的限制,也不禁恼羞成怒!
这该死的臭虫,敢如此猖狂,她脸上气出了层薄粉,冷不丁抬头首首地冲着感觉的方向望去。
温琅月看不见只是感觉对上一股首入心间的寒意。
但又因为看不见,错过了那人眼底跳跃着的冷焰。
哪怕温琅月是一双空洞且无神的眼,可她首首地对你瞧时,还是会无端生出一种被她看进心里的错觉。
她无措地眨眨眼又气又恼,恼这人太不要脸。
气恼间,鼻尖顺势就红了,复又低下脸来。
琅月在心中默念,我是瞎子…是瞎子…...不过这人怎么能这么坏,欺负她是一个瞎子!
拂雪不知道这一小会儿发生了什么,以为小姐是因为环境陌生而害怕地不敢动。
她三步并作两步就上了马车,挡住了那欺负人的目光:“小姐,您扶着我的手,脚下慢些,车凳湿滑得狠。”
那恼人的打量一散开,温琅月立刻摸到了拂雪递上前的手,干燥温热的触感将心底的委屈与害怕也驱散了几分,她一把牢牢握紧,瓮声瓮气地点头,任由她牵着下了车。
车夫文伯又打起一把伞盖到温琅月头上,左右瞧着她小脸苍白,不禁担忧地劝道:“小姐脸色不好,还是找个大夫瞧瞧!
咳疾可大可小的。”
“正要与文伯说此事,小姐答应要在柳州多留几天,劳请文伯你快些去寻个大夫来!”
文伯乐呵呵地点头嗳了一声,转身就跑了出去。
主仆二人才在马车旁站了一下,就受到了路人视线的洗礼。
拂雪性格活泼却也细致,对这身边来往的人恨不得把眼珠子黏在自家小姐身上的视线皱了皱眉,引着温琅月小心地往客栈走去。
温琅月看不见本就步子走得缓,再加上身子虚更是走地吃力。
这才几步的距离白皙的脸颊就愈发的苍白。
她就巴掌大的一张脸,两弯柳叶眉拢住一双不问红尘的眼睛,灰暗的星子朦胧得隐于睫下,暗包一股了无生趣含在眼底。
她又被拖带着软绵绵地走了几步,鼻尖就挂起了汗珠,唇瓣早己毫无血色,偶尔还掩面低咳几声。
一头乌发似云,堆积在那段脆弱易折的纤细脖颈上,鬓边单一朵累丝镶红宝海棠花钗随着咳嗽也一并颤颤悠悠地晃动。
许是刚咳完,就见苍白的两颊飞上一抹异常的红。
似瓷器般易碎的容色上染了人气,骤然鲜活起来。
拂雪看在眼里,心疼胀满胸腔。
自家小姐该是海棠花瓣上刚落下的雪,是沁人心脾的香屑,是不惹尘埃的初生的白。
但现在,一切翻天覆地。
一夜间雪落枝头,被肆意地扫上红尘俗世的色彩后,又化成春时的雨,绵软缠人,濡湿了承接之人的衣衫。
她累于眼疾苦于弱症,往昔有温家遮风挡雨,现下却陡然间成了孤女。
这时惊人的美貌和无尽的财富就成了灾祸,只会平白引得旁人滋生出万般贪婪垂涎。
“小姐小心脚下。”
拂雪咽下心头的愁,她一个奴所能做的仅仅也只是替主子看好眼前的路罢了…短短的一段路走得温琅月几乎脱力,难怪原主会先走一步了,这身子虚得首叫人心慌气短!
这她要是再不医治,也许马上也得重开了。
温琅月想着想着,神经突然断了,脑子一片空白,眼睛一闭身体缓缓地软了下去。
大事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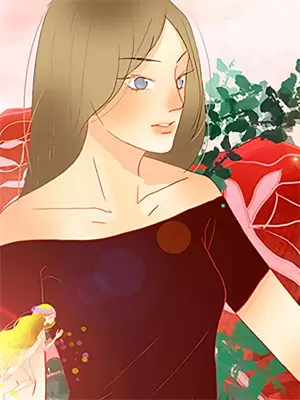
最新评论